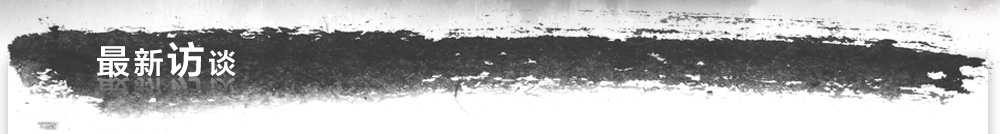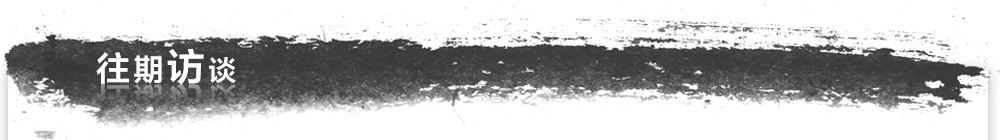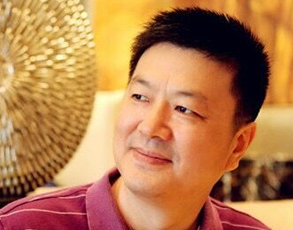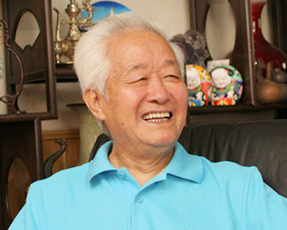刘涛:滤瞳——专访街拍摄影师刘涛
刘涛有双滤瞳,这滤瞳是他的35f2镜头,也是他的灵魂出口。
他走街串巷,如寻母氧。拍照是他的下意识,相机是他的器官,而他的照片,是他“滤瞳”的物质表现。
刘涛生长在合肥老城,拍照之前,从未想过这片城会成为他与世界的一种连接甬道。为了试图消解生活中的各种疑问,他上街看人。各种人。生活在他们脚下流动,他们成为时间的静物。当视界产生一种“黑色幽默”,刘涛渐感“治愈”,用快如眨眼的镜头将他眼中的城市定格。尔后,他被世界上的一些人知晓,人们读他照片中的城与人,感到生活被重新解构。
在刘涛的作品中,城与人的关联被崭新组合,动与静的响应被趣味拼衔。你在其中睇出魔幻,其再为你归还荒诞。当艺术行为成为一种人文道义,刘涛将他的“滤瞳”出借。在他的镜头中,人们得到一副阅后即焚的视网膜,这视网膜,是奔跑着的中国城市的另类天眼,也是更递着的文明进程的上帝视觉。
—“很多人会通过你的照片认知、了解合肥。”
—“不,他们分不清这是哪里。这是中国。”

Vol.1
他每天都在街上走十几公里,当然,与他的相机一起。从拍照那天起,直到您读此文的今天。有时他的大脑与相机都载获满满,有时他一无所得,与城市面面相觑,然后在街角超市独自喝两罐白熊麦啤。
有时他觉得自己富可敌国。市井百态在他心中奔涌,一如大千世界在他心中私构。有时他觉得自己一贫如洗。见过世相陆离,却对生活的真相一无所知。
他不认为自己是“艺术家”,仅是“艺术行为从事者”。他的私人生活几近为零,拍照是正常工作时间之外的全部事宜。“生活在别处”,这个50岁的句子适用于35岁的刘涛。
他在台北与黑社会大哥喝酒,在德国与港籍服务生聊生活。
他有时远观被保健品推销员簇拥的老人,有时会跟拍男扮女装的性工作者。
他会花一下午的时间观察在闹市工地拾钢筋的儿童,也曾看到宠物狗被当街撞死后,主人扬长而去,对犬尸毫无眷留。
大街上充满太多秘密。他有时拍,有时不拍。不拍的时候,他如鲠在喉,照例又去超市门口喝啤酒,看着天光渐暗,这城市将夜,人们的生活浮躁起来。
Vol.2
街道带给刘涛太多。
他与所有进入他镜头的人都素不相识。他当过兵,打过枪的手让快门势如闪电,因此被摄者几乎察觉不到刘涛的镜头。只是常在同样的街巷来往,手持相机,目若搜寻,有人直斥他是“神经病”;有人认为他是城管部门的“眼线”;在电视上得知过他身份的人,质疑他的拍摄目的。垂头丧气中,被路边烤猪蹄的大叔瞧见:哎,你不是那个拍照片的吗,又不偷又不抢的,没事,拍!
刘涛希望这个每日与他在心底幽默对谈、在他的照片中独属于他的城,可有更多包容与宽待。“如果一个人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做出的选择,都能被他人包容,那世界就会更美好。”有人去他微博留言:你拍到我的脸了,照片你删掉吧。再满意的作品,他也选择毫无保留。
迄今为止,刘涛都在抗拒直接介入自己作品的市场化。如同他抗拒将自己的拍摄“使命化”——这一切,都是他与他的城的私事,他拍城,是在拍自己。
欲望?不是没有。只是,定义不同。
“人最终是自私的,比如我拍照,也是自私的,我就是想要个结果,拍照的快门就是一种发射,那一瞬间就像抠动扳机,你总想去带点什么东西回来。无欲无求?不可能。可能我的‘欲望’比别人更强烈一点,并且是不间断的。”
尤其,他的作品中对商业环境的讽刺,被他认定为是一种“批判与消解”:“如果我的照片是面向虚无的,我的人生也应该是这样。”

Vol.3
他还有些从未给第二个人看过的作品,他私藏,暂时觉得不该面世。那是一些在大街上得来的震撼,这些是宝贵的感官瞬间,而他不想“消费”这些痛苦,以让他人贴上各类尴尬的标签。当然,也有可能,这种“震撼”只属于自己。刘涛想,反正他总是走在大家常见的地方,看见一些自己觉得“很不常见”的东西罢了。
拍照快十年。刘涛的拍摄范围,依然是合肥一环内的街角巷陌。城市在变,人在变,只有刘涛的镜头没变。出了这个二线城市的内环老城,他便“收手”。
“在异处我就不会拍照,只靠肉眼观察。因为拍不熟悉的东西,很浅表。”
灵魂对刘涛的纪律严格。有时他想到身边蝇营狗苟的纷扰,会自我安慰:人活着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自己。
然后他出门去拍照。无数深夜工作的底层工作者都曾在渺渺夜色间独自抽烟。这个画面,只有刘涛和他的相机知道。
Vol.4 对话
郭玮:接触摄影之前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刘涛:以前在水厂里工作,有一些相关的爱好。那时水厂里工作的都是快退休的男性,像我这样20岁出头的人很少。我玩的东西他们都没什么兴趣。那时候我喜欢漫画,做一点CG。但是在单位也派不上用场。还有人际交往的问题,我比较直接,人际关系也处不好,所以就一直在做电工。我当时就觉得可能一辈子就做这个工作了,那段日子还是比较苦闷的。
郭玮:后来怎么想到接触摄影的?
刘涛:我有些朋友喜欢拍照,我当时觉得拍照太简单了,还是一直在画漫画,画到2011年,一些朋友不拍照了,就把机器卖给我,当时我用的是那种长焦相机,觉得拍不好什么东西,镜头一会拉远一会拉近,感觉很像在偷拍。我就把那个相机也卖了,去网上找相机。在网上找的时候看到一个日本的街拍摄影师,森山大道,用一个很小的相机,他拍的照片不是我审美里可以看得明白的,很模糊,黑白的,也没有叙事性,颠覆了我这个没接触拍照的人的认知。所以我就查了他的相机,他用的是胶片相机的数码版,要3000-4000元,当时我就想这个小相机又不能拉近、拉远,怎么这么贵,就去搜索资料。 那时候我们这里大部分人都是在楼顶、公园等地方拍城市,但森山大道却在街上拍照。我觉得这样的照片特别符合自己那时候苦闷的、想要追求自由的心情,就决定自己试试。拍了一些照片之后,就觉得一定要分享出去,给别人看。就把自己一个月拍的照片,精选几张,加了音乐,然后发到论坛上去。当时就很受欢迎,就从2010年一直更新到现在。
郭玮:最开始把照片放在论坛的“社会新闻”板块,而不是“摄影”板块,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刘涛:我开始也在摄影圈发过,但是我看了其它的摄影帖子,都是一些风景,当时我做的工作把我的时间限制了,没办法出去拍那样的照片。不过那时我也觉得拍照要去一些没人见过的地方,哪有就在一个地方一直拍的。 后来看到很多的街头摄影师,看他们的观察和理解生活的态度,觉得每个人不论生活在哪里,都是有很多素材的。后来分析下来,觉得街拍是非常昂贵的爱好,需要花很多时间,又没有商业方面的回馈。每个人做事是有动机的,比如你为什么拍这个,这个照片能给你带来什么。街拍是没有任何目的的,有时候你走在大街上想拍一张,你不知道拍什么,没有带着主题去,你面对的是整个城市的嘈杂。如果你想拍一个老城生活,去老城记录下来就好了;但街拍不是,你要往深处走。你去过一次,和你每天都去的地方感受是不一样的。我走过的路,每五十米就有我拍过的照片;在一、两公里的地理长度里,就蕴含了很多很多人的生活了。但生活在里面的人是不知道的,路过的人也看不到。虽然现在是手机摄影的时代,但也依旧很少有人去拍这些。所以综合考虑,觉得自己的照片相对于“摄影”类别,更贴合于“社会”。
郭玮:后来你发现自己的照片被传播开来了。
刘涛:后来我开始在微博发。更新到2014年,《三联生活周刊》就联系到我,希望我能把照片整理一下,他们帮我发,说估计会有一千多人转发,所以我就选了90多张发给他们,结果有五万多人转发。
郭玮:再去拍会被认人出来,这样会不会影响拍摄?
刘涛:2014年后,关于我的新闻铺天盖地,再去拍的时候会被人认出来。最后会有一些思维上的冲突。 比如下暴雨我也在街头拍,一手打伞,一手拿机器,他们就不能理解,觉得现在大家都认识你了,可你怎么还在这拍,没有一点长进。8月合肥气温接近40℃的时候,我大中午也在街上拍照,一条街上路过很多熟悉的人,大热天的,看我一个人也不打伞就拿着机器拍,卖水的人就问我,你这样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啊,我告诉他们这是爱好,然后他们就说你因为这个爱好,马上就要晒死了。 后来我就想到一种解释,比如说那些钓鱼的人,他们钓鱼也不是为了吃鱼,这样说他们就能理解。如果不解释的话可能会被当成精神病,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遇到两个一模一样的小胖子,在旁边拍他们,我当时离得比较近,闪光灯一亮就被人发现了。我就听到那两个小孩说,这个人每天都来拍照,是个精神病。当时我也没办法啊,小孩子怎么解释呢,有的小孩受家长影响,本来玩得很自在,结果看到我的眼神就像看到精神病一样。
郭玮:你照片中的幽默与戏谑让人印象最深,这种风格是自己特意处理的,还是你本人看世界就是这样的眼光?
刘涛:自己拍照的话,还是希望有一种幽默的讽刺感,像卓别林的电影那样,带一点思考。在街头把握一个幽默感是很难的。每个摄影师拍摄出来的风格是不同的,有的摄影师的风格我就拍不了,他们也会跟我说拍不出我这种照片。所以摄影师看这个世界,也是在反映自己的世界。
郭玮:作品里的讽刺感是一开始就有,还是慢慢摸索出来的?
刘涛:最初刚拍几个月就开始有点这种感觉,比如一个雕塑在“流鼻涕”,或者雕塑身上被晒上衣服,就觉得这个东西蛮自然、蛮有趣的,后来对生活了解越多,就越悲观。上个月很热的一个晚上,我看到一个和我差不多的年纪的人在三孝口搬砖,周围都是街景,旁边一个大叔搂着一个年轻女人路过,那个女人和搬砖的人也差不多大。我就一直看着他搬了很久。
郭玮:你的构图风格和你喜欢漫画有关系吗?
刘涛:也有,小时候喜欢《灌篮高手》之类的日本动画片,受到不少影响。选择拍街头的画面和漫画其实也有关系,都是和自己的生活有关的事。
郭玮:平均一天要拍多少张?
刘涛:有时候一天下来一张都没有。我按快门很多次,但有的时候我看见了但相机没对焦好,或者没来得及拍下来。还有电池的问题,我基本出门带五块电池,最后都用完了。大部分时候都像猫寻找猎物一样,要寻找,要观察,还要等待。
郭玮:有没有想过突破老城区这里,在合肥其他地方拍?
刘涛:没有。有的时候会往合肥东门走走,因为我在一个地方呆的时间长了,到其它地方就像到了一个新的城市,不熟悉而且从来没去过,对周围所有的构造都不了解。
郭玮:像这几年很多人觉得很景观化的新城区,你有没有拍摄的欲望?
刘涛:没怎么去过,我也没什么兴趣,我觉得那边每个场景都是固定的,没什么生活气息。包括老城区的淮河路步行街我去的也很少。 我一般都在居民区,或者三孝口书店那边,就是有街区的地方。在那里拍的时间长了你会感受到有气息、有变化,他们的交流你都听得到,他们说什么都在你的耳朵里,你每天去都接受各种信息。合肥有段时间房价涨得很快,那时候你就能明显感觉到,老巷子里的人们都开始有些蠢蠢欲动,不愿再沉下心。这种直观的感受很有趣。
郭玮:在拍摄过程中和拍摄对象聊天吗?有成为朋友的吗?
刘涛:没有。我不太愿意和他们聊天,聊天总有双方兴趣契合不契合的问题。你要是说实话,总会有人不理解你;你要是顺着他的话说,又总是简单两句就讲完了。我参加了一个德国媒体对摄影作品的评奖,我之前在家和一个德国的编辑聊了一夜,然后把照片发过去,评上一个奖,当地有人去看了,还把那个用我的照片做封面的展览劵寄给我,那张照片我拍的是一个卖肉的,我拿着这个劵特别高兴地拿去给这人看,他就一边磨刀一边说了一句,嗯,是我。过了好几天电视放过这张照片之后,他才特别高兴地过来感谢我。然后慢慢熟悉起来我就没办法拍他了。因为太熟了,一路过他就会和我打招呼,一打招呼我就没办法拍了。有的人太熟了,那种很自然的感觉就没有了。有几个大爷大妈在练踢踏舞,他们都认识我了,看到我来了马上就停,等我走了才继续。
郭玮:这些年接触了很多事之后,再去拍街景,自己的眼光、思维、价值观会有变化吗?
刘涛:其实你接触了太多之后再回来,心情有时候会变得不好,你更真切看到很多人忙忙碌碌,其实就是为了赚钱,然后养孩子,希望孩子变得和自己一样或是比自己好,但他们也不知道具体要“好”在哪。这时候街道就会“治愈”你。人们在街道笑得很爽朗、很开心,他们的思维是很直接的。我觉得生活最可怕的一点是,你接触的很多人在过着一模一样的生活。有时候我去一些很好的小学看家长接孩子,有的织毛衣,有的聊天。看完小学之后我就继续往前走,看中学门口,也有一大堆车子。有一次在一个中学门口,晚上十点多钟下大雨,我在那待了一会,拍了一张照片,看到一个瘦瘦的日本大叔,问他的翻译“这是在干什么”,他的翻译告诉他“这是在接孩子放学”,那个日本人就摇摇头。 接孩子上学、放学,从小学、初中、高中再到高考,就像一场轮回,你在中间看到他们不停地循环往复,有一种虚幻感。我也看过一些艺术家圈子里的人,他们也一样在校门口等孩子,大家都是这样,这就会让我有一种无力感。跟我一起拍照的人很多,后来一些购物网站需要大量的照片,很多人都去拍了。我也遇到过一些请我去拍照的,我说我不行,我要去街头拍照。像我这样的,有的人可能他自己愿意,他的家庭也不愿意接受。我在街头有时一、两天都拍不到一张照片;去帮别人拍照,都有实打实的收入,但是你去拍那个,你的照片就是千篇一律了。
郭玮:听你的说法,感觉你是很在意“灵魂”的人,一个是自己的作品要有“灵魂”,另一个你作品里的人的“灵魂”也是千篇一律的,有一种轮回的可怕。
刘涛:但我不想去展示这一点。我想展示更有乐趣的地方。很多人拍唯美风光,很精致,类似商业照片。“商业”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让大家都喜欢,是要把产品推销出去的,不能有自己的意图在里面。我了解我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既残酷也有温情,我不能让大家看到这个世界无比残酷,但也不能满是温情。
郭玮:2016年你出版了摄影集《走来走去》,之后受众有怎样的反映?
刘涛:虽然我拍的是合肥的街景,但这本书在北上广那边卖得更好。我觉得现在合肥还在慢慢变化吧,我能感觉到“90后”,尤其是90年代末的那一代在慢慢转变思维,思想更加丰富,有求知欲望,书店有很多年轻人在看书。但合肥真正注重文化的这一方面还是在刚刚起步。首先做这个事情的人要重视它。以前有一个电台来采访我,一定要说明我有多辛苦,我觉得这思路不对。作为一个媒体人,你不能一直想着宣传生活有多辛苦,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个劳动者。在街上比我呆得久的人太多了。环卫工人、交警这些人在街上待的时间都比我多多了。对方就很不满意。后来我就不太愿意参加这些采访了。
他还有些从未给第二个人看过的作品,他私藏,暂时觉得不该面世。那是一些在大街上得来的震撼,这些是宝贵的感官瞬间,而他不想“消费”这些痛苦,以让他人贴上各类尴尬的标签。当然,也有可能,这种“震撼”只属于自己。刘涛想,反正他总是走在大家常见的地方,看见一些自己觉得“很不常见”的东西罢了。
郭玮:成名后,有没有想过对摄影方式、内容做些改变,或是用名气来做些什么?
刘涛:2014年之后,我出版书、登在杂志上有稿费,很多人就会来问你挣了多少钱啊?但这是没办法去衡量的。所以我觉得我的网名叫“Grinch”蛮好的,“让人失望的人”,可能2014年以后大家会觉得我会不一样了,可是我还是没什么变化。我的微博也不怎么更新,也没微信公众号。
郭玮:有没有联系你要做广告或是推广之类的?
刘涛:太多了,有的私信我看一眼就直接删了。因为拍照是我心里最重要的东西,一张照片他人可能觉得没有价值,但我觉得是有价值的,我觉得它的价值比那些几万块的广告费重要得多。
郭玮:你很抗拒把这种爱好商业化?
刘涛:其实我的想法是很宽容的,但有时候还是对社会上有些急功近利的人反感,我觉得社会上每个人都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我看到太多人都在做同一件事。很多刚开始街拍的人想拍那种人生的“苦”,比如老人捡瓶子,可是别人看到的“捡瓶子”和我看到的“捡瓶子”其实是不一样的,这个问题其实要用两种思维来看,有人觉得老人很辛苦,但其实有些老人家境还可以,但他们就是喜欢辛辛苦苦地捡几个瓶子赚点钱。
郭玮:有没有想过拍类型更多元的人群?
刘涛:我有时也会拍到一些所谓的中产阶级。怎么说呢,有些人物质到了一定程度,但精神其实还没有到达那种水平。比如两辆车碰了,这种事就很容易反应出来素质的高低,我拍到过好几次因为小刮擦事故引发的争吵。包括过马路,有的车就不会让你。不过这几年就会有车让行人了,这个月我就遇到两、三次了,因为我经常过马路,所以感觉很明显。但是“阶层”这个概念,有时候你说不清。在底层生活的人,他们其实不认为自己是底层,他们只是觉得自己这里比较脏和乱。所以不同类型的人在我照片里都有,但是我不会刻意去区分。
郭玮:其实城市一直是发展的,尤其是经济发展,你拍的市井百态,是不是也会根据经济的变化而变化?
刘涛:有的,现在很多卖菜小摊也会用二维码,还有共享单车,有些年纪比较大的人一开始就不太理解,后来慢慢的也会了解、使用。有钱的人、中产阶级、普通的小康家庭和一些生活在底层的人都有自己的开心和不开心,但是他们之间很难交流,我可能会在中间穿针引线,因为我都能看到。
郭玮:作为这个桥梁的意义是什么?
刘涛:主要对我自己是有意义的,看到不同的事情,接触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人的处境。
郭玮:一直拍这个题材,自己会不会觉得雷同,有想超越的地方吗?
刘涛:有雷同的地方。我这种拍照还是很自私的,我不是想把这个城市记录下来,因为我不是职业的,不是一个报社的记者或是要去记录城市的工作,我不是以记录为主,只是拍我自己想拍的,但确实把城市记录下来了。而我拍的不是一个大的、宏观的景象,而是市民细微的变化。我一直跟周围刚喜欢拍照的人说,千万不要带着使命感去拍照,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是很短暂的,“使命感”是要创造属于自己的东西,同时,喜欢一个事物的好奇心不能泯灭,恰恰社会就有很多浮躁的东西,很多利益方面的东西会让你没有好奇心。
郭玮:你认为自己是艺术家吗?认为什么是艺术?
刘涛:我认为我这是一个艺术行为,不认同自己拍的照片就是艺术。 艺术首先不是寻常于大众的,是追求自己心灵的东西。我认为我的艺术行为是我每天行走、观看的过程,我看到了很多事之后产生了思考,拍出了照片,我对我周围的事是有思考和有表达的。我心里一直有一个框架,有一个判断,很多东西是不会妥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