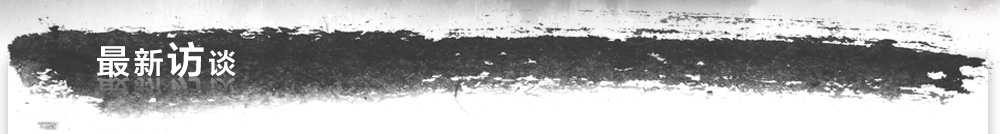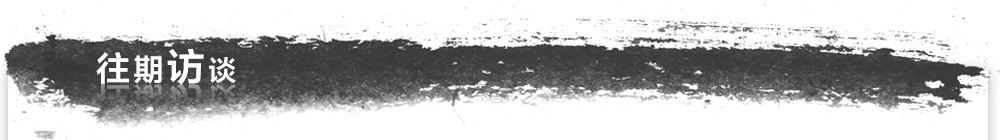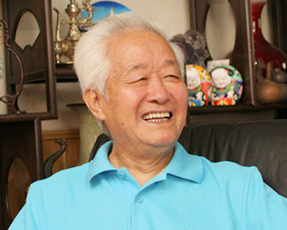吴少东:诗人的另一种面貌——专访诗人吴少东
吴少东合肥生,合肥长,合肥立业,合肥成家,从未脱离过故土,这与人们对八十年代走出来的诗人印象不符。没有“漂泊”、“孤闯”、“远方”、“背走”这些关键词加身,依然制造出了吴少东这样一个总在“怀乡”的古典情怀中徘徊的诗人。自然,这个“怀乡”的“乡”与他诗歌本身一样,身兼多义,成为一种提喻。
他是家乡的狂热推广者——“GDP近6000个亿,在全国省会城市排名前十,人口780万,城市面积11445平方公里,全国前三”,这套话术他对外的介说已无数次。15年前他去北京,从难以想象的堵车盛景一窥北京之大;转眼,合肥也早已是个堵车的“大城市”了。这个一直站在故土之上的诗人望着拔地竞欢的楼厦丛林,感受到生活空间与视维开阔的扩大正比。家乡一直在他的骨血里奔走,一如他的诗中总在印闪的“父亲”的符号形象,成为了他理路和言筌间沉沉的韵脚。
没有坎坷,经历顺意,但并没阻碍吴少东对生活绵绵不绝产生的精神之问。诗歌是他最好的解密工具。他像一个被诗歌选中的人,从规制化的生活中走出,与大多数人一样,却又有所不同;他拥有工具,于是他会站在队伍前面,为后面的人视远。而“吴少东”这个名字,几乎是突然“闯”入多种刊物、诗选和评论家视界的。这其中,又不乏有一个优秀诗人炼成方式的第一百零一种可能。毕竟,生活如水,而我们必须诗意盎然。

Vol.1 与诗歌的年少友谊
诗歌之于吴少东,像夏天午后藏在云卷里的金色光,辗转之后总能映在他身上。初二时,他在《安徽日报》发表了第一篇作品。那是首叫《蓝天上的海》的散文诗,承载着一个从没见过海的孩子对海天之际的幻想。不久,他又发表了《月夜》,描叙中秋之夜思念在台湾海峡相隔的亲人。“那时写诗没考虑过主题升华、政治隐喻,倒不小心促成了一种‘小中见大’。”
吴少东生于阅读机会贫瘠的六十年代,文学的启蒙条件并不优良。能找到的书他都看,《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三侠五义》,或者《欧阳海之歌》《金光大道》,或者《红与黑》《简爱》《战争与和平》,或者《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杜工部集》。“《红楼梦》《古文观止》《战争与和平》和《三侠五义》给我的影响巨大,让我现在的创作都带着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倾向与印记。”
尔后,八十年代来了。北岛、顾城、舒婷等这些朦胧诗人,影响着几乎所有六十年代人的嗷嗷待哺的表达欲,吴少东同样。当然,还有普希金、雪莱、泰戈尔们的抒情与博尔赫斯、里尔克们的深谧。在那个文学青年阅读标配一致的年代,新的诗人在不断觉醒。
吴少东便是之一。当过数学课代表、化学课代表的他,虽然作文一直年级第一,却从来当不上语文课代表。在老师眼中,他的文字有那么一些“非常规”。索性,高中时,他和现在也已蜚声诗坛的同学叶匡政合办“春花文学社”,尝试建立起自己的诗歌理想国。这底气来自在中国诗歌界地位不凡的家乡的启迪——“安徽被称为中国现代诗的延安,合肥宿州路9号,文联大院,曾经的《诗歌报》编辑部,全国诗人心中的圣地哪。”
这个合肥青年一路秉着一种微妙使命感进入大学,并由此进入了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他是校园的风云人物,是学校大学生辩论队的主辩,是系学生会主席和团总支书记,被同学誉为“安大第一诗人”——校学生会把他的诗张贴在整面墙上;校报整版发表他的诗歌作品;安徽大学潜风诗社邀他担任社长,婉拒后难却盛情挂了个名誉社长……1990年,吴少东在心中神圣的、宿州路9号的《诗歌报》上发表了两首作品:《黎明的月光还在清冷》和《沉重的翅膀》,仪式化了他与诗歌的年少友谊。此后,又陆续在国内数十种纯文学报刊上发表了众多诗歌作品,一时名传青年诗人圈内。
大学毕业,吴少东被分配进一大型公用企业做宣传工作;不久又被选调至市委机关负责党刊《合肥工作》,一编就是7年,这本他手里的党刊,每年都是全国十佳。虽然党刊的严肃性、制约性很强,但吴少东仍尽量把文学性填充进去,将一定比例的文学作品,尽力安置在各种领导讲话、调研报告和任免信息的间隙中。
“市领导带队去亳州市调研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我抽空跑去看三曹的旧迹、花戏楼和芍药花,后来还写了几篇散文。在亳州,我思考‘亳州’的‘亳’的由来——亳州是药材之都,农耕社会时,走南闯北的药商,有钱后都爱在家乡盖高大的房子,一是显摆,二是为了保证家中妻儿的安全。亳州又处地势较高的皖西北,‘高’、‘ 宅’两字分取上下,一拼便是亳。当然,这是我个人偶然的思考发现,考古学家不—定同意。”身居不大不小庙堂的吴少东,依然割舍不下这些细碎的人文情结。
同期,他却割舍了他人生一件重要事物。万物都在剧烈生长的九十年代初的中国,在彼时吴少东看来,诗坛却乱象纷呈:“我特别不喜欢‘主义’、流派一类的东西。诗是非常个性化东西,每个诗人都是独立的、不一样的。后现代派在中国也被很多人学乱了,我觉得很多人写的那不是诗。‘五四’以来,很多人不仅没学到西方新诗的精髓,也弄丢了中国古典诗的灵魂,一切只有浮表,靠形式与词句去周旋。所以1993年开始,我停笔了。不再写诗。”
吴少东这一停,索性就停了18年。18年里,虽有历史、小说和传记、笔记一直相陪,依然持有在体制内工作中见缝插针的人文情怀,唯独,不碰诗。

Vol.2 传播之变,与不变的四维圭臬
2010年秋,吴少东和叶匡政等诗人聊天时,听他聊起微博,觉得有趣。回家后,他让儿子帮忙注册了一个。用“前诗人吴少东”这个名字一登入微博世界,他就惊呆了。“我惊异于微博的传播力。但更惊异的是,我的诗人朋友们向我展示出微博对中国诗歌的贡献,可以说,这个媒介为诗歌插上了翅膀,它让诗歌走向大众,迅速传播。短短一首小诗,阅读量动辄几十万,读者是职业各异的网民,而在传统诗歌刊物上发表,你知道你的读者只能是写作者、文学爱好者和专门研究者。”自媒体的形式冲击,加上2010年后中国诗歌在国际上已然进入了第一方阵,宽容、蓬勃的诗歌环境加在一起,让吴少东觉得,自己可以回到“诗歌”的现场了。
而一提笔,他吓了一跳。他感到自己是一个18年没有练过功的武侠,艺生了。“我给自己列了个计划,用六个月时间调整,看书,思考,研读当代诗人的作品,恢复‘武功’。”
我们喝下第一口消暑之水/薅除满月草,打开经年的藏冰/坚硬而凛冽。南风鼓噪/坂坡渐去,你无需命名/这一白亮的现象。就像一条直线/就像平躺的春光/你无法测度它/从左到右的深度。你无需测度
三个月后,吴少东写出了这首被诗人和评论家推为其代表作的《立夏书》。他有些羞于说出“代表作”这三个字,他认为一个创作者的作品应该受力均衡,只一两件被人反复说起,是作者需要自省的问题。
生锈的技艺被砺出了灵光后,他没有“开闸泄洪”,而是谨守着每篇作品出产的秩序和质感。他出品不多,也不快。而《苹果》《描碑》《湖畔》《给予》《孤篇》《以外》《天际线》等越来越多的作品,陆续发表在《诗刊》《诗选刊》《诗歌月刊》等传统文学刊物及微博上。吴少东的名字开始快速被读者和诗歌评论界关注,微博粉丝短时间内涨到了18万人。
除却《立夏书》的自然悲悯,《苹果》的宇宙思考,《描碑》《孤篇》《青石》的亲情挚感,《给予》《湖畔》的格物灵光……吴少东的创作,题材蔓延而落笔行洒,他完成了短暂焦虑期的过渡,成为了一个明确了表达坐标的诗人。他的诗歌作品被选入重要的年代诗选和每年的年度诗选,并连续三年荣登《中国诗歌排行榜》和《中国新诗排行榜》,一时引发诗界热议。吴少东的回归与成果,被一些诗人、评论家们命名为“吴少东现象”。
说起这些,吴少东笑。尽管初二时那懵懵懂懂的两篇发表作品已经预示着他与诗歌将有的暗结,风光澎湃的大学校园也辉映着他的诗间神采,但人到中年,吴少东也才真正领味到“诗人”二字的分量。梁小斌曾说,他在吴少东的诗中读到了“神性之光”,“诗人”这诗化万物的“神性”表达者,一定意义上说,要有自己的规格。
吴少东对自己有“规格”要求。间隔了18年,再度用“诗”表达自己,他感到年轻的自己与现今的自己间,两种感情力度的巨壑:一种清澈,一种沉雄,两种表达风格杵在“18年”这足以成熟一个社会个体的狭长时光的两端,让吴少东尽情体会到了所谓的“中年况味”。他更喜欢这种沉雄况味:“它们更加直抵人心,触及灵魂”。
“情感,美感,痛感,意义。我为这八个字而写诗。”这四维是吴少东诗歌的圭臬,——我厌恶那些虚情假意的空乏感情,这种感情只能用语言去遮盖,用意象去弥乱,让诗歌变成无根之词。我所写的人、事一定是我熟悉的,注入情感的。最怕有情绪没情调,有情调没情怀。——诗是文字的精华,是贵重的,我追求语言内在节奏感、音乐性,写的时候心中就充满旋律。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曾说,‘把诗写晦涩是不道德的’,很多人喜欢用生僻词、自造词营造诗歌的外在美,在我看来,其内在美最重要,词句之外散发的诗意最重要。”
雨声大了起来。吴少东轻询我可否抽根烟,然后起身把窗户开到风会将烟吹到别处的角度,坐下来点起烟:“诗要表达一种怎样的状态呢?有人说我的诗读时会有种痛感,但这种痛感,是当下这个时代造成的,不是吗?人情的淡漠,商业化对道德伦理的冲击,人的价值体系的坍塌……人们心中有痛,却无信仰,这是种人道的内伤。我致力于把表达这种‘痛感’变成写诗的追求——别人读你的诗,心能像小铃铛一样地晃一下,像秋千一样被推荡一下,甚至有更大的震动与火花,这就是我的追求。”
“痛感”之后,“诗歌的终极审美”呢?“我不否定情绪、情调在诗歌里的重要作用,但我还是希望诗歌中有触动人心的东西,比如爱与悲悯。一定意义上说,情绪不是意义,情怀才是;格调不是意义,格局才是。”

Vol.3 “诗人要有‘天眼’,更要有‘心眼’”
纵是吴少东脑海中有诗象四合,和他面谈时,他却不会刻意将诗人度质肆意放送。短发,金丝边眼镜,江淮普通话,整个人抖擞利落,绝不拖泥带水。这和他的“公务员”身份有关。“直到五年前,我的绝大多数同事都不知道我写作,只知道我会在领导讲话稿里用上‘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和‘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样的句子。”
修路架桥,建站筑场,工程立项、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工程初步设计的审查审批……这些反差很大的本职工作与情感敏锐又心有磅礴的诗人身份,在吴少东这里没有冲突感,宏观和微观、精神与物质都聚焦在吴少东的大脑中,互相开拓。“你看,做宏大的建设规划不也是作诗?在大地上出现一个标志性的、改变人们生活的事物,也是创作。”
他善于自我调和,往会议室一坐,他是严谨而高效的人;在诗会上一出现,他就是一淋漓性情者。所以,正式投入诗歌创作后,他就没有用过笔名,他不惧别人因职业对他诗人身份的误解。沉浸在一个场域久了,定会有各种偏执,有的诗人常会抑制不住的戾气,在吴少东这儿不存在。“我有自己的通道。”他说。
更重要是的,诗歌是人类共有的灵魂语言。吴少东的诗存在一种现象,他的很多作品获评论家好评的同时,读者也喜欢。“我从来不认为一首诗被广大读者读懂、喜爱,是令一个诗人害羞的事。反而我非常欣喜,因为我的诗与他们的情感与灵魂是相通的。如果非得让我在评论家叫好与读者喜爱间二选一的话,那么,我选择读者喜爱。毕竟,真正好诗的标准是什么?能打动人,能给人痛感与喜悦,能给人自由的空间,能呈现爱与悲悯。”
诗人、评论家周瑟瑟在给吴少东的评论中这么写到:“他的每一首单独的作品其意象、结构都经过细心安排,给人的感觉是吴少东每拿出一首诗,都有所突破。……吴少东虽还做不到像特朗斯特罗姆那样字字发光,但他至少严格要求自已认真对待每一首拿出来示众的作品。”
“我对诗歌有敬畏感,当成一项严肃而高贵的事业。我创作不求量,一个月最多不超过四首,有时甚至只有一首。”他把每首诗都当做自我交代,这引发必要的痛苦:每首诗都要有突破,要有新的形式和质感出来。优秀的诗人总是不会重复自己,只会追求‘经典化’。
“心设慈悲道场,宽恕宿敌和/无动于衷的水域,也宽恕/庸常的诗句。不指认爱与虚妄,/将一座桥横陈水面之下,抵制两岸/以保持湖的完整与骄傲”……这首《以外》被《北京文学》一名资深编辑看到后,其在微博写到:“读来震撼,把中年况味全部写出来了,作者停笔18年太可惜。虽然他有写作野心,但毕竟失去了很多机会。”我问,她提到了“机会”这个词,18年里可能存在的所有机会,你会觉得可惜吗?吴少东想了想:无非是名气更大一些,但我无所谓。18年来除了诗歌,我还有其它收获,我得到了宽阔的胸怀,健康的思想,深厚的积淀,得到了很多诗歌以外的东西。
今年,他在沉心写诗的间隙,参加了《诗刊》的“青春回眸”诗会,成为《诗刊》七届诗会唯一获选参加的安徽诗人;台湾《创世纪》诗刊主办的“金门”诗会他是座上客,也帮忙张罗一年一度的“桃花潭国际诗歌节”等助推安徽诗歌与外界对话的活动。他对诗歌界的后辈无保留,向外界和刊物推荐安徽年轻诗人,甚至会为年轻的诗人们改诗。
在最后,我问吴少东:一个非职业的严肃的专业诗人的炼成,究竟需不需要“天眼”?吴少东皱眉想想,说,做诗,既需要“天眼”,更需要“心眼”。在日常的事物中悟出“道”来很重要。我常在夜梦中浮上来两个好句和意象,第二天却又记不起来了。后来,一有灵感和核心词句,我就立即记在手机里。这可算“天眼” 与‘ 心眼’的有效衔接?有时一个看似一气呵成的作品,也会被我晾置数月,“感觉”来了再去修改、发表。就像这被这雨水润湿的土地,须待时日的蒸发与吸收,才能达到最佳的自然状态。吴少东望了一眼窗外没有完结的雨,如是说。
在吴少东这里,诗人不需要长久而固定的痛苦,等待收割灵光,后面发生的事,就如余秀华评吴少东一样:“他的诗歌里有光,这光指给你看:这是诗歌。”一切都是自然,让“诗人”的身份烟火化——一个真实的诗人,才是真正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