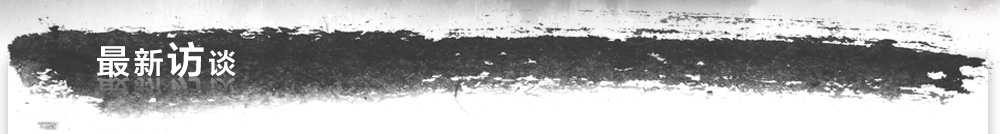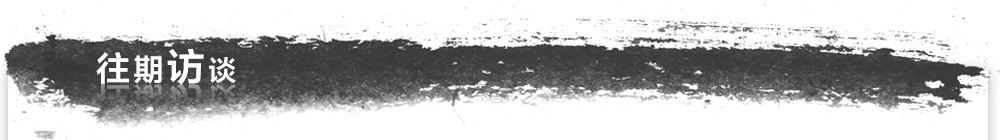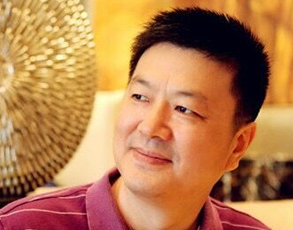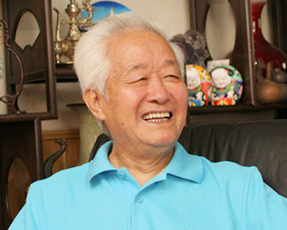许若齐:走出徽州——专访作家许若齐
许若齐自称“徽州遗少”,从极度传统的标本式徽州家庭里“突出重围”,却在出走徽州二十几年后,又提笔写了十几年的徽州。
他认为写徽州有三个阶段,风物、风俗、风骨。而自己目前刚刚突破第一阶段,行文尚停留在“风俗”之中。
从父辈的徽州风骨里出走,成为“徽州”一生的观客与评者,许若齐试图着用“散文”这个美器在传翳文脉间四两拨千斤,终有一天成为“徽州”记录者中,一个不可被忽视的存在。

Vol.1 一个徽州遗少的叛逆
许若齐祖籍在休宁下汶溪,“出县城南门以后就能看见,那是一个很漂亮的村庄。我们下汶溪许氏从道光年间开始到现在,我是第七代,大概几百号人。”许家至今保存着完整家谱,这是大多数老徽州家庭的特征。
在这个宗际分明的大家庭,“父亲”这个词,在许若齐心中,是徽州那一丛丛、一脉脉的山的样貌。
“父亲给我影响很大,但是,他身上还是有不少属于徽州负面的东西。他一辈子基本上没走出徽州。徽州成全了他,徽州也局限了他。”
许若齐看来,父亲这代道地的徽州人,是传统徽州人的代际终结;这一代人以后的徽州人,无论从气质上还是禀赋上都与“徽州风骨”差别很大,已经不具备他们那种传统了——低调内敛,谨慎保守,固守传统,等级森严。“我发现我一方面是继承了父亲的很多东西,另外一方面也在摆脱他的一些东西。”许若齐回忆起父亲带来的生命印记,这个传统的徽州男人,在记忆里为许若齐勾勒出徽州印象:家教严苛,规矩谨严,做事认真,一丝不苟;规律到甚至每一分钟都雷同不变的生活作息,几十年如一日;饭桌上,所有家庭成员的座位多少年都不曾变动……这种规矩而压抑的家庭氛围,让许若齐对父权之下的传统家庭几欲逃离。
这种“逃离”从职业的选择开始。
做了一辈子中医的父亲,自然而然地想让许若齐对中医事业有所承袭,“他认为全天下最好的职业就是医生。对此,我是叛逆的。我喜欢文学,他恰恰最反感文学。”
许若齐在初中时已对文学有了浓厚兴趣,毕业有四个选择:升高中、插队、上工矿、读中专;中专有两个学校可以选择,一个是卫校,一个是师范。许若齐违背了父亲的意愿,遵从自己的兴趣,在“医”与“文”间选择了后者,进了徽州师范学校(即现在的黄山学院)。
在师范读书的一年半,对许若齐有着深远影响。同学们大都是“老三届”的插队知青,文化功底深厚,带来了读书的热烈氛围,和他们在一起,许若齐快速地成长,对古典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初步接触了外国文学。
“73年春天,我们到祁门一个乡村劳动两个月,当时那个地方有一对下放干部,分别来自省文联和省图书馆,住在村里的一个老宅子里。我喜欢文学,对古今中外一些名著却似懂非懂,就和另一位同学去他们那儿玩。老两口会谈到文学,像曹雪芹,吴承恩,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啊,我们也不太懂,他们就借一些书给我们看,这在当时都是禁书。他们鼓励我们将文学坚持下去,这一段经历对我很重要,帮我把文学的门打得更开,文学的世界更宽广。”给许若齐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一生》,讲述一个16岁女孩从修道院出来之后的凄惨一生,故事的力量性给许若齐带来巨大冲击,他甚至记得,读完这本书,他一个人跑去林中坐了很久,脑中一直回想着书中的故事情节,久久不愿离去。
彼时,他已开始尝试创作。“父亲对我写的东西是不大看的,认为我写得不行,没有古典文学的底子。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对于文学的最早启蒙还是来自父亲,他有时会情不自禁地读起唐诗宋词、《古文观止》,我在一旁偷偷地听。那时候看书都是借回来偷偷看,因为文革嘛,有些书属于禁书,他看见我的书就当场扔掉或撕掉,很伤人的自尊,但‘读书’这件事我还是坚持了下来。”
18岁不到,师范毕业的许若齐变成为了一名初中教师;教了两年书,1978年他参加高考,以高出北大当年分数线十余分的高分,阴错阳差进入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合肥,开始了一生的教书生涯。
Vol.2 徽州与徽州写作
除了少年时曾跟在老师后面写独幕话剧,许若齐认为自己真正的写作是从2002年开始的,在《新安晚报》上发表游记《德国小镇》。
他偏爱散文,热衷短句子,简短的速写式表达,流淌着生活情趣的酣畅快意。
“散文文体自由,对于我来说,写的东西比较简短,散文更适宜一点。我写的大多是情趣性的东西,深刻的思想的东西基本没有涉足。像当代的散文作家,我比较喜欢的是丰子恺、梁实秋和汪曾祺,他们的散文更多是表达一些生活场景中情趣性的东西,是内心的一种关照。
可能一定程度上,散文的介质特性,更适合许若齐对待徽州与徽州人的表达诉求。
“徽州人是很中庸的,比较内敛,是‘不争’的。徽州人骨子里是保守的。像徽商走出去了,还是回来了,在家里建宅子、盖祠堂,架桥修路什么的。同是文化厚重之地,徽州出不了安庆刘文典这样的‘狂徒’,出的多是像胡适这样文质彬彬的谦谦君子。”
许若齐认为徽州有着与现代社会发展相悖的一面。从思想文化角度看徽州,许若齐认为徽州是毁誉参半的,比如当下最令人称道的文化元素——徽商,也是封建社会晚期的一抹夕照。“徽商的发展主要依赖官商结合,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发展经济需要良好的竞争关系。徽商走的是垄断的路,排斥开放竞争。再一个,徽州人性格内敛,诚实守信;但传统的徽州人是比较保守的,包括一些文化上呈现出来的对年轻人的教诲,是圆滑世故、谨小慎微的,这在许多古村落老宅子里的对联上可以看见。由此可见徽州人的人格里存在很大的缺陷,至少从社会的下一步发展来看,这些都是不可取的。”在许若齐眼里,这些徽州文化的劣根性,像极了现在徽州那些老败、颓废的村庄,透着一股腐朽的气息,却又代表着当年的成就与辉煌。
许若齐偶尔回顾自己,1982年离开徽州,期间不间断来来去去。在人生过半后再过头看,他自认当年的“走出来”是对的,“走出来”之后看徽州又是另外一种感觉。“我还是很爱徽州的,爱它的山山水水。但是我很多朋友也说,徽州人还是要走出来。你可以生在徽州,阶段性地长在徽州,不能一辈子在徽州。”徽州人的“波澜不惊”,已让许若齐这一辈的徽州人感到难以与外面奔跑着的世界想契融。“以我父亲为例,他是名老中医,救死扶伤,活人无数,晚年摔了一跤,就是不愿意去医院,他对西医不屑一顾,不手术,宁愿在床上躺六年。对外面东西不接受,即使接受也要很长的适应期。”传统徽州人的人生也因此不会有很大的波折与风险——因为他们或许压根就不会去“冒险”。
“而人生很多时候的痛苦是来源于上进心。不对吗?徽州的传统生活注定舒适无害,但我们这一代的人还是想走出徽州,去多接受来自于外界的‘痛苦’。”
有着如此一番对于家乡根性的判视,许若齐的地域写作注定拥有着一种背负。而这也是地域文化写作都需要面对的问题:弘扬家乡之美,也要敢于揭开劣根与陋习的脓疮。
许若齐明白,做到这一点需要极强的思想穿透力,毕竟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徽州虽只是一个很小的分支,想看透其中也并不容易,需要极其透彻地把握到内里众多深刻处。当然另外一方面,“也需要很高的文学技巧。”
多年来,许若齐用自己的散文描摹着徽州的传统风味,记录着徽州的现代即景,《徽州烟火》《一钩新月天如水》《刀板香》《饮食安徽》《晨起一杯茶》……在这些节奏既明快又舒缓的字里行间,他写市井风情的汊口包子店,写嬉水的童年,写多少年不变其中内容的徽州老人的炉上煨炖,写外出务工者渐多后的寥寂的村庄……徽州的寥寥模样,在许若齐的笔下,成为一幅毋需时空逻辑的人文地图,散序而凝练,有时又沉重而悲悯。
在许若齐笔耕不辍描画徽州的这些年,“徽州”也渐渐成为人们谈论起安徽文化的关键词之一,各色文艺作品展现着徽州文化的优美与苦涩,使其成为色彩迷人陆离的文化符号。
“徽州”作为文化旅游目的地之一,因而逐渐热闹起来的现今,许若齐并不意外:“从旅游方面来说,徽州的条件是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同时具备,同时徽州的明清建筑还极其难得地保留着原汁原味。”
已经退休的许若齐,有了更多时间回到徽州,有时是去探旧,有时是去采风,有时只是为了吃,在乡间的小饭店流连忘返,尽享口腹之美,乐不思归。
“我感觉五十岁是人生的一个分水岭,人骤然就会平静安宁下来,一方面是身体的原因,另外一个是我们的社会体制,无论做学问还是做事业,到了五十岁基本都定型了。这时候,如果你之前就是一个‘静’的人,之后就很从容,我就是这样。同时呢,我是写文章的,对于写作的保持,也培养了我的‘静’。”
走出徽州家庭的保守与内敛,在都市生活了半辈子的许若齐又不免觉得,人最难的,其实就是自我内心的秩序与守定。
这个人生的辩证论,想来是有趣的。

Vol.3 许若齐的“徽州美食”
许若齐的徽州书写中,以“徽州美食”的切入居多。
“我一开始写的东西比较杂,而且还带有文革的一些痕迹,现在都觉得不能看(笑)。题材比较杂,包括文革时的一些感受,我的少年时代,还有一些游记等等,写到后面就不大能写下去了,因为就那么一点感受。后来开始写徽州的一些事,徽州的村落,徽州的人,徽州的美食,发现写的比较得心应手,毕竟是很熟悉的。当时也有一些人反应读起来很好,体验很好。于是就在这个领域专注下来了。”
许若齐的第一本书是《夕阳山外山》,十万字中,徽州部分占了三分之一,而这一部分他自认写得最好,读者反响也好。他想,与其乱写,不如写自己熟悉的,那就写徽州的一些东西吧。尔后,他对徽州美食的观察和记录愈发痴狂,相当大的书写篇幅都在徽州美食上。而写美食的意义,不仅仅是在写美食,更多还要体现美食所蕴含的文化韵味。
“徽州写了这么多年,没有太大的突破。”许若齐苦笑,“我自己总结,地域散文写作,第一阶段是写风物;第二阶段是写风俗;第三阶段是风骨,这是我当然也不仅仅是我,很多作家都很难突破到第三个层次。一个非常成功的作家,都带有很大的地域性,像莫言,陈忠实,写的都是他们的故乡。但凡是成功的作家,他一定要把当地这种‘风物’和‘风俗’上升到‘风骨’,就是文化深处的东西。我还是不行,但在向这一方向努力,但凡是写作,都要经历这个。但要突破这一点非常不容易,思想要有很强的穿透力。我写了这么久的徽州,还只是在‘风物’这一阶段,接触到一点点的‘风俗’。”
而作为文化核点颇多的徽州,许若齐将笔触聚焦在“美食”之间,以一方至味写意世俗人间。
何况这美食之后,牵动着自然地理与人文底蕴的悠长渊源。
“徽州人喜欢吃咸货,是因为徽州人节俭,腌火腿利于慢慢吃;再比如说喜欢吃辣,因为山区里面,山高水寒;另外徽州食物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便于储存,把吃的时间拉得很长,比如干笋,这和山里物资不丰有关。”许若齐聊起美食来,像是在聊一位故乡老友。
“徽州菜重要的是火工,讲究文火慢炖,这和徽州多山、多木材有关,柴火充足。徽州菜很精细,徽州人对吃很讲究,这和徽商的夸奢斗富、慕悦风雅、见过世面亦有关系。现在的徽菜和过去相比差很多,一是现在食材大多都是人工养殖的,二是烹饪功力。徽菜对食材要求太高,真正做好的不多。”
而徽菜最名声在外的三道名菜:臭鲑鱼、毛豆腐、刀板香,在许若齐看来也不是没有“槽点”。“毛豆腐其实并不是很好吃,外地人之所以来徽州都要吃一下毛豆腐是噱头,大多是游客是为了体现自己由此了解了徽州文化,真正喜欢吃的很少;臭鳜鱼还是很不错的,但现在真正野生的鱼很少了,味道上打了折扣;刀板香要想好吃,还是需要真正农家的土猪,腊月里杀了以后,腌好晒好,吃的时候首选五花肉,很香。我父亲很会吃,以前乡下的朋友会送腌肉给父亲,我们自己家也买新鲜肉回来腌和晒,但我父亲一吃就说不行。主要是晒的功夫没把握好,早上几点拿出去晒?晚上几点拿回来?是很讲究的。我父亲说,晒得不好,有一股热晒气,我到现在没有明白这句话。”
《刀板香》在几年前成为许若齐一本文集的名字,也在几年后成为他被读者聊到其作品时提到最多的代表作之一。“那里面满意的作品不多,也就十几、二十篇吧。写吃的东西不能就吃写吃,要写得有趣,就需要一些小故事、小包袱。”他写“刀板香”这道菜,就写了父亲对“刀板香”的要求,还写到了世事变迁,在写作过程中也自觉有趣。一道菜,成为一个徽州人的人生之根,也成为这个徽州人的文化之魂。
接下来,许若齐想写一写家乡的新安江,他有意去书写这江边的一切微小,如无名的小村庄,或者村庄里的船工、木匠、和尚,甚至是江里的一群鸭子。许若齐希望以这些微观世界的折射,来尽可能接近自己心中对“风骨”的追求。
“你在徽州那样一个看上去似乎永远静止的地方细细地观察体验,就极容易发现一些很小的事,这些小事各个都具有味道,折射出一种传统徽州人的‘意思’——内敛保守,自得其乐,总有自己的一番内心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