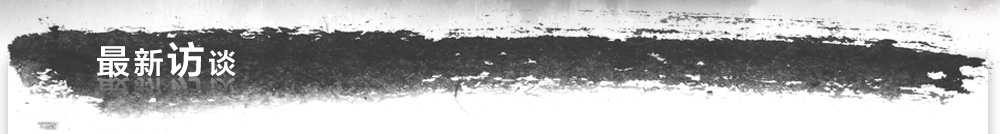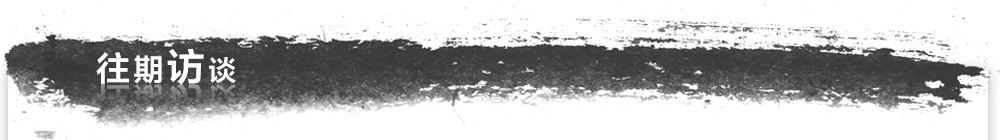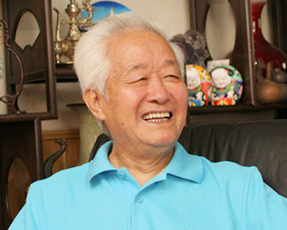闫红:与“恐惧感” 浮世同行——专访作家闫红
和闫红对话,我的身体从直坐姿态,一点点前倾、前倾,最后几乎要半身趴在方桌上,向着那密麻语速的主人扑面而去。
闫红说话飞快,话们紧锣密鼓地抓着你。她善于自嘲,行语爽快,每一份回答都成为引人入胜的人事速写与快照。更重要的,她有着北方式的真诚感,这与她一直存在的笑容一起,让你感受到一个以“写人评事”而卓名的女作家的本真。这与之前在饭局上遇到的她有反差萌。排除纯粹对话的空间环境,闫红容易给人一种莫名诱人的小小疏离感。
我想,这可能与这一个小时的“纯粹对话”中,闫红说的最多的词——“安全感”有关。
“安全感”是她于生活、于写作所索的唯一物。这成为她自我气质的一种封印符号。而封印的解锁,便是她内心,那一道异色的“恐惧”。

Vol.1 早上那十点钟的大街
按现在的说法,闫红有着一个很酷的青春。
她高二发现自己对“上学”这件事已经失去兴趣。中考作文是满分;可到了高中,数理化成绩奇差。闫红开始觉得,这样下去是浪费时间。“我很早就对自己的人生产生忧虑:如果成绩差不多,上个差不多的大学,回阜阳托托关系可以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在小城市安逸的一生就此可以铺展完全。但我不要这样的人生。”
如果不去“主流”地上学,还能干什么呢?父亲为闫红指了条路:去读复旦大学作家班。“我爸对我有着奇怪的信心,他对我毫无来由地信任,由着我做任何想做的事。但是那时候。我只是一个在报纸上发了几篇文章的孩子。”
父亲是记者,闫红从小就被他教导一种“写作者”式的思维方式:面对一件事,要学会叙述它。父亲和她聊往事,家里长辈聊八卦,她有条件反射,一边听着,一边在心里把那些家长里短组成故事。
“我从小生活环境里见的人非常少,包括现在我也是这样。我匮乏于和大多数人的深入交往。阅事也少。所以对世界的认知只有通过阅读来弥补。相对于真实的人,我对书中的各式人更有感触。”
在复旦“作家进修班”的两年,闫红最大的收获是安安静静看了两年书。偶尔发表文章,发的最多的,是用闫红的形容,在当时还很“静态”的《萌芽》杂志。
那是林白、余华、陈村和王安忆正当红的90年代,安妮宝贝等网络写手带来的千禧语言革命也尚未来临。闫红热衷于描写个人生活的传统散文,而这在当时并不受欢迎。“那时很狂妄,觉得复旦的进修也满足不了我了。进修一结束,上海我也不想呆了,直接回了老家。”
“小城市干工作都讲究关系户。”闫红接受了这种环境的安排,在父亲介绍下,暂时成为一本机关内刊的编辑。那年闫红二十一岁。“我知道这一切不是我的未来。走在早上十点钟的大街上我常常就恐慌,不知道这辈子能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看着那些十八九岁的人就很难受,我想我已经不再像他们那样年轻了,我一定要立即去做点什么。”
她又开始写作,依然是散文。频繁投稿间,闫红与省城的诸多报纸建立起联系,一些编辑开始关注她。在一个记者朋友建议下,闫红来到合肥,报考《江淮晨报》,成为一位报社编辑;一年后,经朋友介绍进入《新安晚报》副刊部。

Vol.2 与“人”相通
没有文凭的闫红在合肥遇到了很多欣赏她的人。对于一个自觉性格有些棱角的人来说,她知道自己幸运。可在高人林立的报社,闫红一直在意着自己没有学历的出身,及惶惶不安的写作方向。这样不安而焦灼的日子,她过了四五年。直到网络写作时代的写作机会,涌到这个年轻的写作者面前。
“大概2003年,我开始在天涯和中青论坛发文章,读者在帖子后面直接向我表达鼓励,我写得更有劲了。”在此期间,闫红一组解读《红楼梦》的文章常被挂到天涯首页,网友反响热烈,留言无数,出版社的约稿也纷纷找上门,其中不乏中华书局这样的老牌出版社。最后,闫红和第一个找上她的出版社合作,在2005年出版她的第一本书:《误读红楼》。
“那几年书业境况不大好,这本书只卖了几万册;但对我的生活来说,却带来了一场刷新。我找到了写作的自信——这是我生活的依赖。”
闫红将这本书寄给著名作家王蒙,希望得到些提携,但也没敢奢望太多。没想到王蒙很快给她回了邮件,并且给她写了一篇五千字的书评。这篇书评成为《误读红楼》再版的序。之后几年,王蒙也曾应邀出现在闫红的新书发布会上,罕见地为年轻作家站台。“他是一个给了我很多帮助的人,这毋庸置疑,但我们现在仍然是不熟,无论是王蒙老师,还是我自己,都不习惯于用太热络的方式与人交往,即使互相欣赏。我喜欢张充和的那句‘十分冷淡存知己’,总怕过于亲密会给别人带来困扰。我跟很多人都是这样。”
自认不善经营人情世故的闫红,一直坚持写“人”,并一路酣畅。图书经纪人纷纷找上门。2007年,解读民国名伶的《他们谋生亦谋爱》出版。其后,《哪一种爱不千疮百孔:张爱玲爱过的那些人》《诗经往事》《周郎顾》《如果这都不算爱:胡适情事》……闫红几乎没有停滞的时光。
“可慢慢的我感到,写书的人越来越多,写作者的出版价值在被渐渐削弱。”2013年初,腾讯“大家”专栏的合作找上她。作为曾经的网络写手,她惊讶地发现网络写作已进入付费时代,网络不再只是一个展示作品的窗口。
闫红对网络写作有感情:“网络写作能检测出读者的兴趣点。比较好的写作状态是你写的是自己感兴趣的事,读者也有共鸣。”她认为自己文章最鲜明的特点是“保有观点”,“我尝试用现代眼光来看待各色书中人,将现世价值观连接,让读者得到自己生活的收获。”这些在她的文章名中可见一斑:《集邮女星多姑娘为何放过贾宝玉》,《“暖男”贾琏,温暖地杀你》或者《秦可卿与王熙凤之间的谜之黑洞》。

Vol.3 时刻与“恐惧感”对抗
“网络,是我这个现代写作者最重要的介质。”闫红说。
可网络中,对与读者互动的把握,相当微妙,“迎合写作”很容易成为一种面对商业世界的妥协。闫红认为这是她极力在克避的地方:“‘互动’可以避开写作者自说自话的可能,你会对生活有很多了解。对传统写作有基础、对写作发展有野心的人,是不甘于沦陷到这个处境中的。你会在你感兴趣的话题中,找到别人关心的点;而不是先进入别人感兴趣的点再来说话。”
从书业式微到“鸡汤文学”热销,闫红十几年的出版经历恰遇这场图书市场的起伏。这些年来,她坚持写着《红楼梦》的各种评文,今年刚出了一本《十年心事梦中人:红楼梦中的情怀与心机》。她发现,这些年来,她写“红楼”的文章,点击量一直不低。“这个时代依然有人愿意读这样的文章。”闫红想,“如果你在你的写作里,找到人性的共通点,是能给别人带来一些影响的。”
她渐渐也开始被邀请评写娱乐圈的人事陆离。对于一个写《红楼梦》人物的女作家,自带扫描属性的视角很适合这种“乱花迷人眼”的书写对象。闫红的娱评主观性很强,她会由着自己的感受,描述郭富城高调炫爱:“他的肤浅,是我们少年时代留下的路牌”;张柏芝,她写:“‘做自己’这种词只能放到广告里,不是每个‘自己’都能讨人喜欢”;明星分手后引网友唏嘘旧人,她写:“同情弃妇是另一种全民恶意”……每一笔果敢火辣,是泱泱鸡汤和八卦中的眼球爆点,也是这浮世的一份独立宣言。
就如她往古典文学里加了一把流行文化的味料;她在流行文化里,也腌了些深沉的后调。
这些老辣而高频的写作,使闫红那携自少女时期的“恐惧感”稍稍松缓了些。这些年来,她一直与这种“恐惧感”对视与对峙。“我对生活总有一种忧患感,时刻担心被时代、被生活所抛弃。我知道有风格的人是不会这么想的,而我就是很俗。”身边也有不需要太努力,顺着家境安排便拥有慵懒生活的朋友,而在闫红看来,那种人生她也无法苟同:“我不愿过行尸走肉的生活,也不愿意让自己陷进过于艰辛的生活底层。”
这种与恐惧感的抵抗,会不会酿就一种“野心”?闫红回答得很干脆:“我对生活的要求太低,不被它抛弃即可,而不是跃在它之上。我的虚荣心不算大,对物质要求不高,也没想成为别人羡慕的那种人,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成功人士’。”闫红过会又想了想,将自己可能存在的“野心”,落点在自己“写作者”的身份上。对于写作,她有终极理想,那就是终有一天写出自己满意的小说。
身边的朋友常常催闫红:你为什么不写小说?“我面对小说,还是不能完全‘放开’。”小说成为未来写作的一种磁石,可以吸着闫红继续这样积淀地写下去。她想写皖北乡土,想写家族沉浮。她和我说起一个五十年代的故事:一个女性在“婚姻自由”的口号被提出之后,在男权世界怎样从“旧女性”生生而被动地过渡成“新女性”;而原型,是她的一位远亲。“这个女性对她人生的处理方式,有明显的淮河人的特点,彪悍,神经质,很有意思。”构思中的人物有着打破“恐惧”向新生的沧海桑田,闫红说起“她”时,带着一种犀锐的悲悯。
Vol.4 “大音希声”
目前,闫红有着繁多的专栏与约稿。这是她目前最大的时间输出。
我说,这个时代需要“专栏”这种块状化的阅读,这满足了大众读者嗷嗷待哺的碎片时间;但对作家本身而言,会不会影响其写作的成长与进程?
闫红想了想:如果说影响,可能也是作家个人的问题。我人生的最大问题,就是害怕“面对”。
从论坛发帖写到门户专栏,这个对“网络”有特殊感情的女作家迟迟没有开公众号,倒成一件现代写作者的“稀事”。而这仅仅因为她害怕这种繁琐“面对”;到了2015年,当整个世界都在聊公众号,闫红才觉得是不是应该也开一个了。于是,她和朋友陈思呈两人共同开了一个号,名字就叫“闫红和陈思呈”。但即使是两个人共同运营,更新频次也是寥寥,成为这个微阅读时代特殊的自媒体文字客。
今年的出书计划多与“整理”有关。《诗经往事》和《如果这都不算爱•胡适情事》两本书今年再版,另外还有一本写人物的书约。
闫红计划着最近重读名著,重新“解读”名著里人物。“《简爱》里,男人对待‘新欢’描述自己的妻子是个疯子,而这对那位妻子来说,其实是场不公允的缺席审判;比如《飘》,郝思嘉拒绝对她一往情深的白瑞德,对艾希礼爱恋了半生,可她自己是否明白那种‘爱’究竟是什么样的感情?我想把这些人物情感,以自己的方式重新梳理、书写。”
她依然想继续写“人”,歪着头想了想说,“不写人你还能写什么呢?”这个“焦虑患者”对充满着“人”的外世渐渐勇敢,惧懦在慢慢消散。“在写作中一定要做个勇敢的人,把心中最真实的一面写出来。比如《红楼梦》里我很喜欢袭人,但在2005年的时候,这个观点是很多主流评论不能接受的,认为她伪善、奴性。但我现在还是坚持喜欢她。”闫红喝了这场采访中的第一口茶,在对话的结尾这么说。
我想到她在写袭人的文章结尾的那一段。“这或许是我对所有的‘义正词严’都保持警惕的缘故,你不知道那些滔滔指责背后,有着言说者怎样的诉求……无数话语组成流水线,将人与事向前推送,离真相越来越远。大音希声,静下来,才能浮出真正有价值的声音。论大事是这样,评判一个袭人这样的小人物也是这样。”
她现在这么看待这个世界。“恐惧感”依然在她身后,只是成为了她的警世恒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