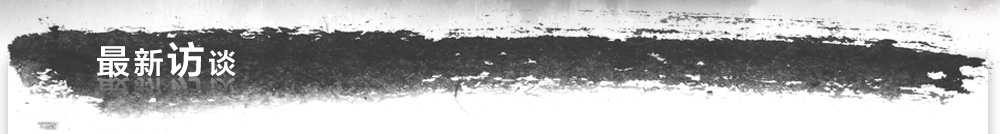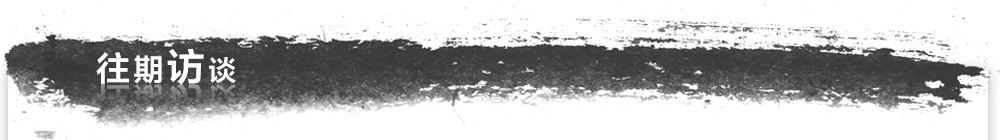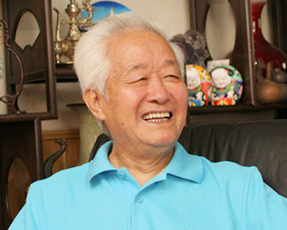祝凤鸣:蓝色乡野的持烛者——专访诗人、文艺评论家祝凤鸣
很多年后,祝凤鸣依然能看到那杵立在摩挲天幕中的人。那人持烛在正午,日头戚戚,心有霹雳。
27年后的今天,为了当代先锋文化在一个二线城市中的驱化,他也如手持烛火般,立在这星斗飞驰的奔跑中的城市里,耀燃前路,铸光于明。
他总是出现在这城市中几乎所有的当代艺术活动中。发言,主持,帮忙招待记者以及各路相识或不相识的艺术家。他曾给一个当代艺术展览起名“冷光源”,说自己喜欢这种对立而又温和的冲击。这有点像他本人,幽默与才情贯穿在他与任何人的所有对话中,让你感受到一种炽热的格调;但同时,他也为自己保留一份诗性空间,在他任何一段语言的句号后,可能一个转身,他就遁到自己的一片清幽宇宙里去了。
盛夏午后,在祝凤鸣将赴爱丁堡签证的忙乱中,我和这位诗人、评论家、策展人、乡村观察家及世界公民,聊了个长天。

Vol.1 乡村少年
祝凤鸣出生于宿松县凉亭镇一个“黑咕隆咚”的乡村,他大二那年,村里才有电。镇上倒是通电早,但走到这个早通电几年的镇子上,还有两公里。
父亲是乡村木匠,母亲是要强农妇,下有弟妹三人,祝凤鸣对乡村那清贫而寂黢的童年生活记忆深刻。捡蘑菇,打猪草,他会去危险的地方:“黑暗,有蛇,但那里往往收获最大”;翻红薯,其他孩子们东捡西拾,他知道笔直走到底是丰收的最优路径:“长大后我读到弗罗斯特说的‘未走之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隐蔽的地方往往有惊喜。”
他总是最早做完农活,跑到草垛旁看《西游记》,世界的鸿蒙因这本书在幼年祝凤鸣的眼前展开,齐天大圣成了宇宙之花。他开始拥有奇妙幻想。高中时,中国迎来改革开放,祝凤鸣学校的阅览室可以接触到外国杂志和世界文学书籍了。强大的好奇心将他与浩如宇宙的外部世界紧紧联通。在安徽西南边陲的贫困小镇,一个乡村少年在小小的学校阅览室里,会为泰晤士河边一场浓雾里的别离而感动良久。
“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说,我今天用手写作,就如同我父亲当年弓腰废力地挖泥炭。我常想我后来的人生不是很喜欢热闹,可能和年少时在农田边躲着读书的求静心有关。”名利表面的热闹,祝凤鸣不爱参与,觉得“不适”;几乎所有的诗歌活动,他都回避。更多时候,他躲在家里两万多册藏书堆里,与书中各方神圣交汇。
他的格趣喜好到了今天也不算主流。读书喜欢先锋文学,艺术喜欢当代文艺,建筑、摇滚、戏剧或独立电影。他刻意让自己保持静默,让行为、社交或思想尽量清绝。以至于在时代与生活的各宗变化之间,祝凤鸣一直是静止的,将身边的所遇挑拣。

Vol.2 从哲学到诗歌
高考,因时代原因,祝凤鸣被调剂进入安徽师范大学地理系。这在他看来也不是不得了的事,毕竟那是在1980年代,“三轮车上都会卖尼采与弗洛伊德”。祝凤鸣在这西哲狂热的时代如鱼得水,将自己潜浸在图书馆,与广阔新天地中的前人际会。“哲学这东西很有趣,你看,叔本华和海德格尔是哲学家,而诗人里尔克、特拉克尔、荷尔德林又成为重要的哲学资源。”智哲们成为一种磁极,赠与祝凤鸣可以时时去打量世界的“陌生感”:“这些如胎记般携带着哲学禀赋的人,给我带来的思想启发是开天辟地的,令我引颈日常人生的本体探究,让我在任何处境中都可以‘完成’自己。”
他开始尝试表达,使用的介质是八十年代同样如荼的诗歌。19岁,读大二的祝凤鸣写了人生第一首诗,主题是母亲手执灯火在山坡送别他的情景。“那个年代青年热血沸腾,很多人热爱书写历史、命运等题材,我对于这首小诗,当时有着浅浅的自卑。但后来我才知道,我真是骨子里就偏爱质朴甚至是‘贫乏’的诗句。”他对诗歌愈发着迷,1984年,祝凤鸣与同学一起创立安师大“江南诗社”,诗社里同好济济,发展茁壮,一度成为“全国四大诗歌社团”之一。
祝凤鸣在校园中的“风云”程度,曾在小他几届的校友——作家常河的一次闲谈中生动鲜然:“那时祝凤鸣已毕业,1989年回学校做诗歌与哲学演讲,黑格尔啊尼采啊,谈吐飞扬,气宇轩昂,加上将近一米九的个子,总是惊艳全场。大家都拿现在看‘男神’一样的眼光看待他。”
作为“风云”人物,祝凤鸣在毕业前,已在校团委提前帮忙了两个月,等着一毕业便正式留用。结果临近分配,却被告知因安师大当年留校名额已超出三位而作罢。简单的静默后,面对机会众多的工作分配,他赌气似地选择了离家最远的黄山市(昔日太平县,今天黄山市黄山区)。就这样,他成为了乡村中学的一名地理老师。
祝凤鸣又回到了乡村。一切好像没有改变过。课上,他对那些和他相同出身的孩子聊星座、聊地球;课下,他把工资花在两件事上:一是买书,《美国当代诗选》《美国现代诗选》《金枝》成为他的心头最爱;二是旅行,西北、高原或者云南、四川……他的一些重要诗歌作品如《枫香驿》《白石坡》等,纷纷诞生于这一自由而无束的时期。
24岁的祝凤鸣渐渐通过在《中国作家》《诗歌报》《诗刊》等刊物发表诗歌小有名气,与他同刊作品在《中国作家》上的安徽诗人,还有当时尚在人间的海子。《中国作家》自1988年开始连续推出他6组诗歌,这些全国性的文学杂志带给祝凤鸣众多机会,不久,他的诗被人带往波兰及日本,后被陆续翻译到了多个国家;北岛主编的《今天》也曾在头条刊发过他的组诗。
为了拥有更好的写作机会,1992年,祝凤鸣离开中学讲台,从马鞍山来到省城《诗歌报》工作,而其时的《诗歌报》在蒋维扬主编下,无疑是中国最为先锋的诗歌报刊;1993年,因为在全国性刊物大量的发诗经历,祝凤鸣被调入安徽省社科院,专职做社科研究。

Vol.3 诗人与诗
多年来,祝凤鸣出版过诗集《枫香驿》,写过美术评论集《山水精神——洪凌评传》,并参与社科院课题,在《安徽通史》《合肥通史》《安徽历史》《当代安徽简史》等重要历史著述中承担过数十万字的撰稿,还写了20余万字的美术评论及学术随笔文章。2013年,他独立编著了一本40万字的《安徽诗歌》,梳理了两千多年来的安徽诗歌历史。
他对“诗歌”有一种担当感,这种与诗歌的亲密责任感基于对诗歌的特殊理解。
“20世纪以来,诗歌已经变成重要的哲学资源。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之后,世界本体用传统的逻辑解释不了,你只能从语言的灵光中来寻求。每个时代的诗人有不同的形态,在今天,诗歌早已不是浪漫主义的激情抒怀,一个诗人,如果没有探寻存在的抱负,没有碎石机般击破世界的企盼,你肯定只能成为一个普通的抒情诗人。”
有人说祝凤鸣的诗“秉持博爱与泛神论情怀,不仅关怀人,还关注着万事万物及其魂魄”——祝凤鸣在诗歌及诗歌以外的世界,都保有一种纯粹的、密如夜色的乡村关注,诗人梁小斌将其称之为“玄塔世界”。与这星球上的人类聚落相对应的,是那些常常出现在祝凤鸣诗歌中的天象、星座、矿物与植物。地理学给他带来了驳杂学识,理科思维也为他的文字带来了精准与科技化气场。“我看文章,会把精准度看得比文采重。语言逻辑链要强劲,这构成语言的内在速度。某种意义上,修辞是下流的,一点点文采,一点点似是而非的感觉,我认为最不重要。”
对语言的这种要求,考量人的心智。祝凤鸣认为,文学创作“由情而发”这毋庸置疑,而“情”实则分为幽深之情和浅薄之情,更多的还是需要对宇宙人生的深深洞察。“一棵树的根部,岩石的分裂,星球的转动,这些容易被我们忽略。有人只写花啊、露水啊、叶子啊这些表面的东西。只写‘涟漪’而不写‘水体’,更不写‘淤泥’甚至岩层与地幔……文章的智力因素一定是第一的,文采的灿烂倒在其次。”
最近十几年来,祝凤鸣诗写得少。如今还常有热爱诗歌的年轻人在文艺聚会上共读他的诗,有人会嗟叹“可惜他现在不怎么写了”。祝凤鸣对此也有感叹:“诗歌一如星空,现在成为一个遥远的安慰性力量。”
Vol.4 独立艺术,纪录片,及比较文化
“请忽略你眼前的这个中年大叔,真正的他生活在繁星之中……”这是祝凤鸣微信的签名,我笑说,是不愿接受自己是“中年大叔”的现实吗?祝凤鸣哈哈一笑:是有点,所以我跨龄、跨界去做些事,我现在除了书斋生活外,与八零后、九零后在一起的时间多,合肥做实验戏剧、独立电影、独立音乐的那帮青年很多和我是朋友。年轻人会喊我去看最先锋的演出,我也会为他们的事鼓与呼。
祝凤鸣曾兼职在安徽电视台做过十年纪录片编导。所幸当时栏目组有良好环境,撰稿时,他会在脚本中尽显私人情致,比如拍安徽尉迟寺考古,他追问时间的本质、空间的错位,字幕中引用奥古斯丁《忏悔录》中关于时间的思考,或者海子的诗句。电视台同事在一篇关于他的文章中写到,祝凤鸣只要一到乡下采访就莫名地亢奋,或指着湖水说:“你看,那里有一只大象在水上行走”;或仰望山峰自言自语:“一匹白马就要飞奔下山”;又或抡起笨重的三脚架念念有词:“我叫你不快活……”他相信万物有灵,也给身边人带来劳苦中的乐趣。
祝凤鸣的有趣,是种骨子里诗性情怀的表达。他的诗性敏锐度已从“诗歌”渐渐蔓延到他的各个表达介质中:由其与同事方可共同编导的电视纪录片《我的小学》曾获得“金熊猫”最佳人文纪录片奖,成为安徽台作为版权单位的第一部“金熊猫”获奖纪录片;2014年,离开电视台多年的他,被邀请参与后来获奖无数的央视大型纪录片《大黄山》的撰稿工作;电影论文《新现实主义电影的锐度与广度》获“第二十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优秀学术论文奖”;2014年,祝凤鸣请来民谣歌手周云鹏与王娟,及近百位中国颇具影响力的诗人,在合肥做了一场民谣诗歌盛宴“圣马之夜:诗与歌”;今年年初,他策展“冷光源——2016中国合肥首届装置艺术展”,这是安徽第一个装置展,也是全国罕见的单纯的装置艺术展,参展的大多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当代艺术家;安徽诗歌界与艺术界的活动,他多有身影,帮忙奔走或做学术主持。
最近,祝凤鸣忙着把中西文化中的“新”与“旧”糅合并尝试更新。“我曾在英国湖区华兹华斯博物馆看到一个香港艺术家做的装置艺术作品,是关于华兹华斯与松尾芭蕉的行吟诗对比:一边是鹅毛笔英文横排工整书写,一边是日本文字的竖排草书;一边是西装革履,一边是禅服与蓑衣斗笠。这两个人其实相隔了一百多年,但因都常常在水边与山径流连,共鸣出一种别样的穿越神会。”这契合着祝凤鸣的想法:做文化需要做出新意、深意,更要有全球意识与视野。
这同时也辉映着祝凤鸣对于“比较文化”的热衷。他一直在试图寻找文化要素点之间的秘联。“我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很少蔓延至世界范围。比如很多人说萨满教,那萨满教与中国东北当然关联密切,但与俄国西伯利亚是什么关系?‘saman’一词,恰恰源自西伯利亚满洲—通古斯族语。历史是个生命体,世界的历史生理总是血肉相连。人不仅要有国家感,还要有‘行星感’,不能让世界文明的关联被人为切断。比如日本学者写中国史,会将整个史前文明的东亚形态完整写出来,这就叫视野开阔。现在全球化时代,更要有行星意识。”
Vol.5 忙碌的“世界公民”
这位向往“世界公民”状态的人,作为国际文艺交流顾问,与朋友们策划让安徽徽京剧团在8月下旬远赴英国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徽剧《惊魂记》改编自莎翁悲剧《麦克白》,作为今年爱丁堡国际艺术节正式参演剧目,将以高亢激越、气势豪壮的舞台表演惊艳英伦观众;他也试图倡议把宣纸与抽象摄影、装置艺术等结合,部分相关工作正在推进中;经他引荐,一位原籍克罗地亚的版画艺术家,正与皖南一下旅游机构洽谈,秋天准备成立一个国际艺术中心,以当代表达激活安徽本土文化……
“中国文艺需要更多的碰撞与激活。”祝凤鸣说,“真正的文艺,是雪国与血泊中升起的黎明,也是黎明中隐含的诗意。拯救文物、保护非遗等,是首先要做的事,这样,传统才延展,有延展才有新生——我曾在一位画家庭院中,看到过一颗移栽的老梅树枯死了,但神奇的是,它的根部冒出了新芽,这几枝新芽我们可得小心翼翼呵护,其葱绿成长还得赖以远方来风。”
接下来,祝凤鸣有些学术随笔、电影评论、美术评论等方面的出版计划。他有太多观点要在自己的书里说出来,等着有人像三十多年前、十几岁的他一样,在这些书面前与他对话。
“正午的持烛者/站在宁静的日光下/和善地,孤独地/没有护送的人……/持烛者,看见天边古老的天幕/微微晃动的蓝镜里/人的火红的嘴唇/倾诉着悲哀。”
有次山区行路时,祝凤鸣看见路边有棵孤立的大树,他写下了《持烛者》一诗,以此表达自己的心境。这心境随着诗歌的流传而愈加深沉,有时候他觉得自己能看得很远,有时又觉得,只能看些近的,比如身边的城市。虽然依然不大适应热闹场面,祝凤鸣还是希望热络于艺术的人可以在合肥这个城市多起来:“我不会因为他人与我的兴趣、观点有冲突就抵触,从事文艺的人在整个人群中就那么一丁点,还争斗什么呢,彼此爱惜与团结才是要紧。文艺对一个城市太重要了。”
一个下午的时间,祝凤鸣没有停止对我的回答,也没有停止抽烟。蓝烟飘荡,如天幕一角。日光沉斜,而灯火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