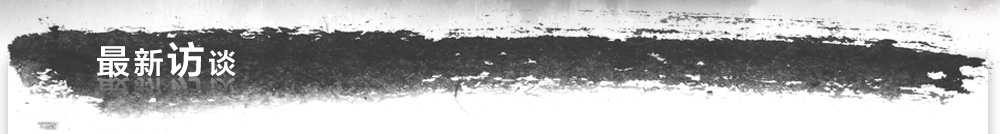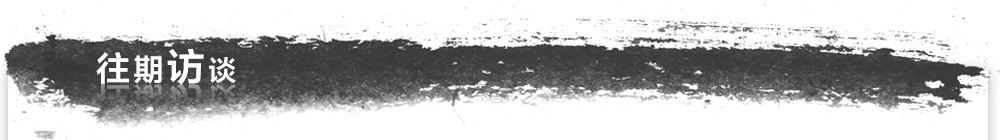谢泽:从无“使命感”的艺术纤夫——专访艺术家、“崔岗艺术家村”发起人谢泽
说起谢泽,本想设计一个很酷的开头,比如“谢泽坐在繁忙的黄山路上的他的黑色普拉多里,深色系地等着我,沉默如谜”,但是文档一打开,还是不自觉地把片头这样铺开——
合肥庐阳区城郊西北三十岗乡“崔岗艺术家村”,一个本该被拆迁成平地的村庄,目前独孑地嵌在合肥最好的一片郊野风景中,氛围盎然又安逸。你站在村口或中央,小店门口几个唠嗑老人,黄狗在你身边绕圈,你只管大喊一声“老谢!”,一定会有人把你领到靠北路东一院子去。那是谢泽的“瓦房”。他总在那儿。
“谢泽”和“崔岗艺术家村”这两个名词总是捆绑着,在媒体和文青口中循环滚动播出。一定程度上,谢泽是合肥文艺圈大动静的指南。他总有陆离举动,满足着这个城市暂时娇羞的文化欲求。而他自称是个“混子”:“生活和艺术都不需要‘英雄’和‘英雄主义精神’,永远不要野心勃勃”。1997年开画廊,2011年合伙咖啡馆,2013年发起“崔岗艺术家村”,其间策展摄影画画写文章,他做的事儿都像在玩;但在合肥,他做的事儿总是先锋。这城市现代艺术发展的纤绳,他手上有一根。

Vol.1 “公众审美是文明的重要组成”
谢泽从小和外公亲。外公周辛夫是张治中在巢湖开办的黄麓师范学校第一任教员、黄麓附小副校长,擅长书法和篆刻。国破家亡之时,流离他乡,以街头为人篆刻为生,倒将这种艺术自成一家。时任国民政府委员的戴传贤题字:“淮南辛夫治印”,以表敬誉。这幅题字如今和经历文革后零星保存的外公书法、拓印,一起被镶裱在谢泽家中。
受外公影响,童年的谢泽会将外公的篆刻磨平,自己学着刻章;认真观察、把玩外公的手作,感受其间的细美。评价起被录入“巢湖地方志文化名人”的外公,谢泽说,“他是个雅致的人”。外公成为谢泽的审美启蒙。
“审美”,在谢泽看来,是民族语境的稀缺词。
“你看,机场、高速公路、高铁、商场、成衣、公历……我们目前大型的公共设施和既有的生活秩序是全盘西化、‘拿来主义’的,外部审美来说,没什么问题;但一涉及细节,就缺乏美感。结构、色彩、材质,不讲究。”谢泽认为,这是民族审美基因的问题,从古就有,三国时代的厚重战甲,美学模式搁在罗马,还是远古时代的水平。”
“中国人的审美训练是不够的,或许因为中国人的心里充满胆怯与对外界的戒备,比如大街上满眼的防盗窗,做得再美,本质也是一件不美的事物,‘美’一定是自由的;再溯之,国人不大具备公共意识,‘个体’鲜为‘公众’考虑,缺乏道德‘底线’。这样的民族心理及社会环境中,文明创造力就被遏制了。文化修养,就是遵从一种社会秩序。这是基本,是民族的文化基因。”……

Vol.2 “艺术要创新,审美要模仿”
我提到现在的年轻人喜欢日韩和台湾的审美流行,并热衷模仿。谢泽觉得“模仿”是好事:“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经历过一段全盘‘英’化的审美秩序混沌时期,一百年后逐渐有了民族烙印强烈的现代美学风格。不过呢,日本的设计虽然很好,但目前新兴流行事物的体系都是美国建立起来的。所以一种好的开放体的文明是跨越维度的。艺术需要创新,但现代审美确实需要模仿和学习。”
畅聊起现代艺术的创新递进,谢泽熟络而兴奋,塞尚的“解构”、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康定斯基的“抽象”、杜尚的“达达主义”、博伊斯的装置艺术……“艺术的螺旋式衍变都是超越世俗与创新传统的。艺术意识人人都需要具备。”
谢泽玩摄影,这也是他最著名的身份之一。前几天忙着参与把一个叫“浮世相”的现代摄影展从北京搬到合肥。早期拍过一组“城市地理”,选址多为城市新兴开发的偏僻处,路上一半荒凉一半繁华,最后变成他平视、慢门的空镜头,“人”只以虚晃的人影偶尔出现。这是他对现代人文的展现方式,也是对摄影艺术的自我解读……

Vol.3 “合肥还是不够大”
2003年,谢泽为《新周刊》写过一篇叫《合肥:彼此都知根知底》的约稿,大意为你走在这城市中,路人甲乙、一草一木,你都了然。十来年后,曾经小城变成了环路拥围的繁华“霸都”。就如合肥人自己都知道的一样,“霸都”,暂时还是种自我戏谑。
“合肥还是不够大,‘怪人’还是少了点,所以像我这种人近年曝光率就有点高(笑),其实做的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翻来覆去地说。”
这些“小事”,大多是为现当代艺术的各种奔走。谢泽坦言,合肥目前做现当代艺术的年轻人,有些“自由得荒芜”,因为得不到足够的关注和呵护——当然,这也是全国现象。
“在合肥,商业发展和原创文化的双重弱势加深了对现当代艺术的漠视。创造性的东西,还是应该被鼓励。好在国家现在对文创产业有倾斜政策,文化被‘商业化’也是好事。‘商业出道德’,是现代社会文明的基石。‘商业化’成熟后,公益与文化产业的结合也就不遥远了。”
Vol.4 由“崔岗”想到以后的十五年
2013年,谢泽亲手在三十岗乡崔岗村搭起工作室的时候,合肥人还处在“大建设”成效初现的兴奋中,大家有了星巴克,有了酒吧街,有了此起彼伏的高架和商场;然后人们在视频采访里看到,谢泽在一个没怎么听过的村庄的简陋小院里,动作娴熟地拖拽着一口老式陶瓷水缸,摆在自己满意的角落,表情认真而陶醉,像在插花。
之后的几个月,这个村庄成为城市热词,二十多个艺术家、文化商人、文艺青年和谢泽一样进驻这里,租座院子,做起了工作室。到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庐阳区对文化产业的重点支持项目;谢泽的“瓦房”工作室,也成为各个艺术沙龙、展览的发布主场所。
“崔岗村的发展,完全是计划外的事。最开始只是图个房租便宜,适合弄工作室或仓库;可是,这个城市里居然有很多人和你有一样的需求,大家的文化准备和心理准备都在促成‘崔岗艺术家村’的慢慢形成。这是件水到渠成的、自发的事。”
有没有“带动文化”的“使命感”?我笑问。“完全没有。文化行为不需要使命感,也不可能被传染;文化也最不需要扶持,是最适合野蛮生长的。”谢泽不假思索。
“合肥的艺术资源有限,好玩的事大体都是同一拨艺术家在做。合肥的艺术市场是有的,但现代艺术的市场还需要等待。目前合肥已经涌起一些年轻的现代艺术买家,预示着这场等待是有希望的事。”……